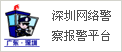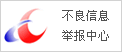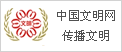被“前首富”们坑惨!民企暴雷引发金融多米诺,锦州银行成风控反面教材

一笔近95亿元的汉能贷款,最终压垮了一家资产规模曾超8000亿的城商行,揭开了一场民企风险传导至金融机构的连锁反应。
2023年1月20日,锦州银行以1.38港元的股价完成了它在资本市场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这家曾在2015年12月以4.67港元风光登陆港股的东北城商行,在历经9年资本市场浮沉后,终于走向终点。
2024年4月15日,锦州银行从港交所退市,成为中国银行业史上首家退市的内资银行。
2025年10月26日,锦州银行发布公告:经批准,工商银行收购承接锦州银行的相关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和人员,双方已签署《收购承接协议》,标志着这场由工银投资、中国信达、长城资产作为战略投资人,历时六年的风险处置宣告结束。但其遗留下的1500亿不良资产,还需要长城资产消化很多很多年。
01 资本盛宴背后的隐患
锦州银行成立于1997年1月,曾与盛京银行、哈尔滨银行一同被称为东北城商行“三剑客”。
2015年12月,锦州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东北地区第三家登陆港股的城商行。2018年,锦州银行总资产一度攀升至8459亿元,跻身全国城商行前列。
然而,与同期曝雷的其他高风险金融机构不同,锦州银行的危机主要来自其民企股东和贷款大客户“爆雷”的连锁反应。
据报道,问题主要出在锦州银行行长——张伟手中。在张伟执掌锦州银行的17年里,他一手遮天,控股多家民营企业,并利用锦州银行的信贷资源,向千疮百孔的不良企业放贷,为银行埋下巨雷。
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灵璧石骗局”。2017年,中国青旅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青旅实业)及下属子公司苏州静思园公司,找到时任锦州银行董事长张伟,请求其帮助解决8亿元短期贷款。
为将贷款“合理”化,苏州静思园公司及中青旅实业作为联合承租人,依靠4块灵壁石(评估方曾给出11.06亿元的虚假评估)等租赁物,成功从锦银金融租赁获得租赁借款8亿元。但贷款到期后,静思园公司及中青旅实业仅支付少量利息,本金及大部分利息一直拖欠,最终宣布爆雷。
中青旅只是其中之一,据锦州银行披露的年报显示,其连续踩中的“爆雷”的民企包括宝塔石化、华泰汽车、东旭集团、忠旺集团、汉能集团等,而这些民企的当家人都曾是多个地方“首富”,也是锦州银行的前十大股东。
这些资本大佬们在风光时相互帮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朋友圈”,而当他们的资本帝国相继崩塌时,与之深度绑定的锦州银行也被拖入泥淖。
伴随着窟窿的越来越大,最终,锦州银行风险全面暴露。
02 贷款黑洞的连锁反应
锦州银行的风险积聚,与昔日的光伏巨头汉能集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该行招股书披露,汉能集团在锦州银行的贷款余额总计94.61亿元,包括与汉能挂钩的受益权转让计划、该行发行的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及保本型理财产品三类信贷资金。
这些信贷资金以汉能集团的港股上市公司汉能薄膜的股权作为抵押或担保。
2015年5月20日,汉能薄膜发电股价闪崩紧急停牌,市值蒸发超千亿,实际控制人李河君从首富“宝座”跌落。
连锁反应立即波及锦州银行——原定于当年6月上市的锦州银行被港交所要求补交与汉能集团的信贷细节,导致首版招股书失效。
除了汉能集团,与汉能关系匪浅的宝塔石化在该行的授信额度为37亿元。
而2018年这两家公司均遭遇资金与债务危机,先后进入破产程序,这对锦州银行的资产质量造成了致命一击。
03 风险爆发:从年报难产到流动性危机
2019年,锦州银行与包商银行、恒丰银行一同被定为高风险金融机构。
风险信号最早在2019年5月显现,当时锦州银行宣布2018年年报延期发布。
在2018年5月的最后一天,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向锦州银行辞任,并在辞任信中直言称,其在审计期间注意到锦州银行向其机构客户发放的某些贷款实际用途与信贷合同不符的情况。
当那份被一再延发的2018年年报终于披露后,市场看到了触目惊心的数据:2018年净亏损45.38亿元,而在前一年的净利润还高达90.9亿元。据年报显示,该行巨亏主要来自高达236.84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不良贷款率从上年度的1.04%猛增到4.99%。
随后,锦州银行出现同业负债集中提前支取、多家同业机构停止授信、同业业务到期不能续作等同业“挤兑”现象,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
04 化险之路:工行领衔的“两步走”救援
面对锦州银行的流动性危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制定了“两步走”的风险处置和改革重组方案。
据中国证券报此前报道,2019年7月,央行会同银保监会指导工商银行、信达资产和长城资产以受让存量股份方式入股锦州银行,为锦州银行提供“增信”。
其中,工商银行通过子公司出资30亿元,受让了10.82%的股份;中国信达受让锦州银行的内资股股份,占该行总股本的6.49%;长城资产拟受让该行部分存量内资股股份。
当时工商银行行长谷澍表示,工行投资入股锦州银行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来出资;二是这笔投资的不确定性要可控,风险不会有外溢性。
风险处置的第二步措施即通过资产重组,同时增资扩股引进优质股东,增强锦州银行资本实力,修复其资产负债表。
2020年,成方汇达、辽宁金控也加入处置。2020年9月30日,通过转让内资股、引入战略投以及剥离风险资产等操作,锦州银行改革重组正式落地完成。
2022年6月末,成方汇达成为锦州银行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7.69%,辽宁金控、工银金融资产、信达投资、长城资产等分别持有该行6.65%、6.02%、3.61%和2.86%的股份。
2024年3月,新一轮重整启动,辽宁金融控股集团接手成为第一大股东。4月15日,锦州银行正式从香港联交所退市,成为内地首家在港退市的银行。
同年10月,锦州银行最终解决方案定调,由资产规模庞大、风控体系严密的国有大行——工商银行全面收购承接,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将不受影响。
如今,工行正式收购锦州银行,这意味着一场原本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震荡的风险已被逐渐化解。
05 风险传导:民企多米诺骨牌效应
风险化解不仅是资产的处置,更是治理机制、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的全面重构。工行入股后,向锦州银行空降了新的董事长、行长等核心管理层,重组董事会,彻底扭转了原有的公司治理乱局。
同时,锦州银行内部启动了严厉的风险资产清收和问责,对风险形成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和责任人进行追责。
而锦州银行的案例也揭示了民企风险向金融机构传导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与以当地财政局或国企控股的城商行不同,锦州银行股权极其分散,股东多达百家,且除锦州财政局外,主要为民企股东,这为内部人控制提供了条件。
这为内部人控制提供了天然的机会。自2009年以来,锦州银行股权变动频繁,一批后来暴雷的民企资本系,纷至沓来。
这些民企股东既是锦州银行的股东,同时也是其大客户,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将银行资金引向自己的产业版图。
当这些民企大佬的资本帝国在去杠杆的监管导向下,纷纷资金链断裂而跌入债务危局时,锦州银行的风险也随之爆发。
06 风控启示:从锦州银行看中小银行风险防控
从一时风光两无到近乎破产被收购,锦州银行的案例为中小银行风险防控提供了重要警示:
(1)公司治理是根本。锦州银行风险核心在于其分散的股权结构和虚置的内部治理。部分股东入股动机不纯,不仅为获取融资便利,还企图将银行作为“提款机”。这些股东同时作为银行大客户,通过复杂的关系交易,将银行资金输送到自己的产业版图中。
(2)信贷集中度风险需严控。锦州银行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民营“大户”,如汉能集团、宝塔石化等。这些企业多处于周期性行业或资本密集型领域,抗风险能力较弱。经济上行期,这类贷款可能带来高收益;一旦经济下行或行业政策调整,违约风险将集中爆发。
(3)流动性管理不容忽视。锦州银行负债结构高度依赖同业融资,而非稳定的核心存款。2019年包商银行事件引发同业刚兑信仰打破后,市场对中小银行风险偏好骤降,锦州银行迅速成为流动性分层下的受害者。
总结
工行全面收购锦州银行,为这场由民企暴雷引发的金融风险化解画上了句号。它警示所有金融机构:在民企大佬风光无限的盛宴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风险黑洞。
未来,中小银行必须回归主业、服务本地,在明确的战略定位上构建与自身规模相适应的精细化风险管理能力。
正如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所强调的,要“稳妥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减量提质”,这预示着中国中小银行将通过一轮深刻的供给侧改革,实现“减量提质”,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来源:万联网

下一篇:看点剧透!已集结15位实战大咖+100余家央国企,①借鉴10+国企供应链+产融实践案例,②业务对接合作,③转发免费领白皮书